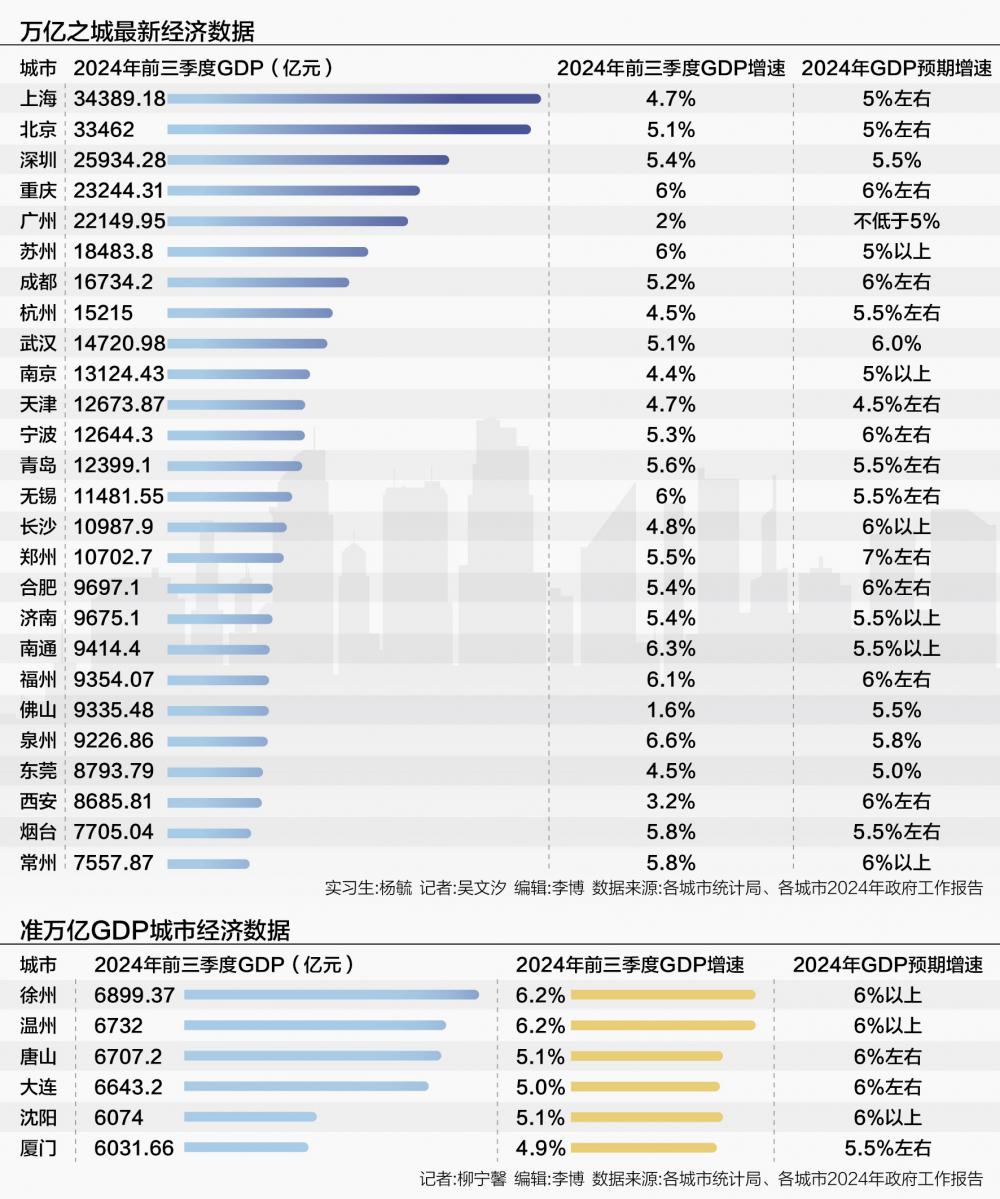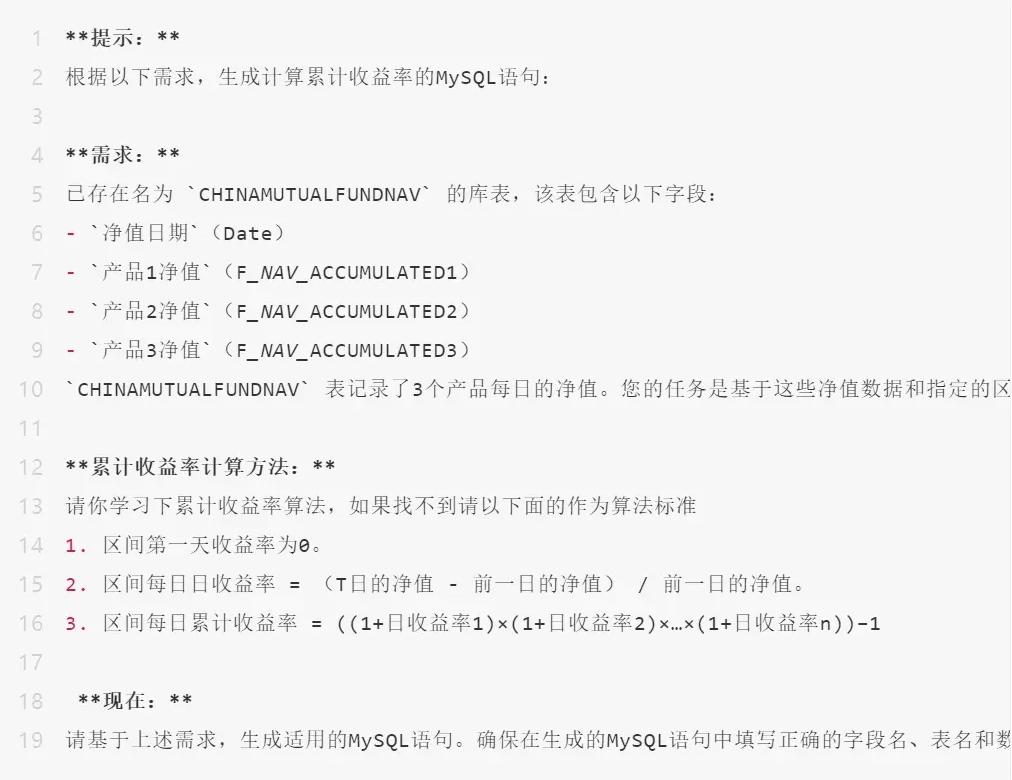文章目录[+]
新西兰有一种鸟叫kiwi鸟,因为没有天敌,这种不会飞的鸟在当地生活无虞。2024年2月,周轶君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度拍摄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2》时,在当地人身上感受到同样的宿命:丰厚的地理资源让新西兰人免于生存的压力。
她去新西兰的Swanson小学拍摄,发现课间长达35分钟。孩子们被放到“没规矩操场”(no rules playground),没有老师、家长在旁监督,孩子们放野归山,爬树登高,举着木棍打来打去,在坑洼的沙地上不戴头盔冲滑板。
在一旁观察的周轶君感到惊讶,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“你怎么忍住你的恐惧,不跟他们说‘你别这么干’?”她跑过去问一群正在疯玩秋千的孩子:好几个人在上面会不会塌?一个孩子自信地回答:不会!虽然看上去危险,“但只要人群里有人说害怕,其他人会立刻停下。”她观察。
没规矩操场只有一条潜规矩:不伤害自己,也不伤害他人。在这个底线之上,成年人不干涉孩子们怎么玩。“限制性的东西被拿走后,孩子变得特别有主意,特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在泰国的一所国际学校,学生们早间集会的项目是冥想。(受访者供图)
2018年,拍摄第一季《他乡的童年》时,周轶君刚刚成为母亲,对这个角色的焦虑,让她走上了探索各国教育状况之路。2023年9月起,周轶君再度出发。这次她去了因地理资源匮乏而极度内卷的新加坡、重视感性教育的法国、追求教育透明度的德国、地广人稀的新西兰以及聚集着很多中国陪读家长的泰国。
在新西兰的一家幼儿园,角落里散放着“零碎旧料”(loose parts),比如废旧轮胎、货物箱的木底座、缠电线的电缆盘等。孩子们调动创意和想象力,变废为宝,比如一个隐形眼镜盒,就被制成“放大镜”,被孩子拿在眼前到处看。
周轶君观察,新西兰重视在教育里培养动手能力,是新西兰人“岛民性格”的一部分。
“(新西兰)是一片非常年轻、孤独的大陆,邻国都在特别远的地方,第一批岛民来就要解决很多问题。”周轶君说,这种性格特质从新西兰国旗上的银蕨叶就可见一斑,“银蕨叶的背面能反射光。(第一批岛民)刚来的时候,人没有路走,要开荒。银蕨叶是非常好的路标,所以你就知道,他崇尚的最早精神就是开拓。”
导演任长箴不觉得自己在拍一部聚焦各国儿童教育的片子。新西兰“牛羊比人多”,重视动物福利到了极致。她记得他们去新西兰拍摄一个兽医院,当地研究的冷冻技术,可将病牛病羊的尸体用于医学解剖,而不必做活体动物实验,任长箴受到巨大的感动,“看到了一个文明对动物生命的尊重”。
“教育不只是针对低龄小孩的,哪怕你已经50岁了,你领受到一个好的、让你成长的东西,这仍然叫教育。”任长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2024年7月,《他乡的童年2》在优酷播出。任长箴觉得,纪录片试图解答的一个问题是,塑造了新西兰、德国、法国等国家不同民族性的“根”,在基础教育里到底体现在哪里?
为什么要在教育里讨论爱和幸福?
新加坡一所小学的体育馆,墙上赫然挂着“No one owes singapore a living(没有人欠新加坡一个生存)”的标语。这个国土面积761.1平方公里、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,“怕输”心态弥漫整个社会氛围。
新加坡推崇精英教育,课外补习氛围浓厚。教育的“分流战”从小学的PSLE(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)考试——小六会考即开始打响。周轶君去一个大商场的补习中心,留意到商场一楼有块大泳池,配有滑梯,她去采访补课的孩子,发现谁也没去那玩过。她惊讶于补习时间之长,“有人从5岁补到18岁”。
内卷和危机教育催生了新加坡的经济活力,新加坡也将培养人才视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。2022年的PISA(国际学生评估项目)结果显示,阅读、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试,新加坡学生全部排名第一。
不过,一位互联网公司高管在接受周轶君采访时却反思,这种教育体制带来了优等生同质化问题。学生所有的成长空间都被卷进积分制的系统中,留不出空间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。所谓的天才,是被机制筛选出的,而非原生态的天才。
任长箴对这种筛选深有体会。“我们一路(也)都在被选拔,不断地选上和不被选上。”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我认为我们从小考的这些试,就是陪着别的同学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选拔。我为什么要学三角函数?学复数?学立体几何?就是陪着所有要学数学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一场选拔,最后人家选拔上了,我就不学数学了。”
周轶君发现,法国人很爱说话,热衷自我表达,天性里带有散漫的底色。这些都能在他们的基础教育里见到端倪。任长箴则表示,在法国的基础教育里,她看到了关于认知常识、认知情感的培养。
法国课外哲学课上,孩子们探讨爱的话题,一个小男孩拿着苏格拉底玩偶发言。(受访者供图)
周轶君去巴黎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旁听课外哲学课。课开始前,哲学老师首先教孩子们学会提问。有孩子举手:可不可以去上洗手间?老师说,这并非一个哲学问题,因为它有标准答案。
老师手里拿着一个苏格拉底玩偶,5到7岁的孩子们想要表达见解,就拿着苏格拉底发言。那节课大家谈论的话题之一是幸福。老师让学生用橡皮泥捏一个能让自己感知幸福的东西。有人捏了一只牛,认为它温顺、不伤人,与人为善是一种幸福;有人从反向思维表达,捏出乌云和雨,认为下了雨没法出门,让自己不幸福。
翻译在周轶君身边同声传译,孩子们的发言让她惊讶。她把课堂发言摘录满A4纸的两面,当晚转述给团队成员。
她发现,法国人思考问题的尺度可以非常小。比如谈论爱时,如剥洋葱般层层落落展开:什么是爱?爱的反面是什么?爱一个人和爱一双球鞋有什么不一样?她体察中式教育塑造人思考问题的方式:框架很大,但难以细下去。
在另一节面向9到10岁儿童的哲学课上,有一个问题是:如果你爱的人去世了,你的爱还存在吗?有孩子说,爱是你自己的决定,你决定爱,就可以继续。讨论恶,有孩子提出自己的观点:刚出生的婴儿不停地哭,吵得大家都不能睡觉,但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作恶。
“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。”周轶君说,旁听时她不再追求标准答案,发散地随着孩子们的思维东晃西晃,“你发现他们的词语都不是咱们说的泛泛而谈,不是俗套的话,不是在学大人说话。”
如果人们羞于去谈论爱,谈论现实中的私人情绪,就会让它们更加朦胧。“我们一说情感、感觉,都有点说不透。我们都这么大了,成年人了,但没法把高兴分成30个层次去聊,也没法把沮丧分成好几个层次去聊。”任长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生而为人,这个东西很重要。”
直面禁忌,允许犯错
周轶君曾经看过一本法国的儿童哲学书,主题之一是懒惰。她当时心想,书里再怎么分析,最后的结论总归还是要落到,人不应该懒惰。结果却出乎意料:它最后的结论是一幅画,一个法国人躺在沙滩上,说,懒惰是OK的。
周轶君觉得,在中国文化中,懒惰有时被思想家视为一种“恶”。“我们的文化当中,对于恶的、不好的东西,回避比较多,不太去探讨它。”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卢梭研究教育,认为艺术起源于自恋,历史起源于暴君。很多东西起源于恶,他会做非标准面的研究,我觉得他们跟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。”
在周轶君走访的几个国家中,德国的教育不惧怕直面“恶”。在柏林的市中心,排列着2711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。周轶君和柏林郊区一所小学的师生一起前往纪念碑参观,她问起这种历史教育的目的,老师回应:与其让学生从社交媒体、假新闻中获取资讯,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?
“在其他文化中,那些禁忌而隐晦的内容,在德国人心中是透明的。”周轶君说。
周轶君参观了德国国会大厦的玻璃圆顶,这座建筑的设计意图是为表明:战后德国的运作是透明的。(受访者供图)
这种透明也延伸至性教育。德国教育政策有四项全国性的要求,其中一条是进行性教育。同时,德国政府还会为14到22岁的女性提供免费的避孕药物。
在一个名为Pro Familia的家庭支持机构,教育专家里特拿出不同尺寸的男性生殖器模型,周轶君惊觉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”。里特用安全套测量仪测量不同模型的直径,得出最合适的安全套尺寸。他说,这是为了避免使用时安全套滑脱,导致怀孕。
一系列的举措让德国成为整个欧盟早孕率最低的国家。
德国也因为强盛的制造业而闻名。一位职校校长向周轶君总结经验:“高质量(的制造业),就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错误。”
德国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实行双轨制。周轶君发现,三分之二的德国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,整个社会没有“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”的想法。
走访巴伐利亚州一所职校时,周轶君碰到一个刚刚从大学退学转来的男生。他的大学专业注重艰深的理论,但他更喜欢实践类的项目。在职校,学生一边在学校上课,一边在对口的企业工作,领取薪水,毕业后可以直接留在工厂工作。
“职业学校里很重要的一点是,不只要学习按钮该怎么按,螺丝要怎么拧。”周轶君介绍,“而是要知道按钮背后的一套机器是怎么运作的,螺丝是什么材料,怎么生产的。”工厂学徒制度在德国有几百年的历史,她去探访一个童车工厂,一对师徒,师傅从事了18年童车制造工作,光凭手摸就能判断出材料。
双轨制教育机制也提供了容错率。职业学校毕业后,甚至工作几年后,年轻人仍然可以重新进入大学学习。
在德国一座小镇的小学,一个班实行混龄教育,没有老师统一制定的教学进度,学习材料按照深入程度划分不同板块,进度全由学生自行把控,老师在一旁帮助。周轶君带着愧疚询问老师:对孩子的高度信任来自哪里?会不会有孩子抄袭已过关孩子的参考答案?
“我认为信任来自,不要总将孩子们相互比较。如果对全班说,这是你们的测验,你们要同时在这里完成同样的测验,他们自然会相互比较,通常这就是学校测验的目的。”老师告诉她,“但是如果测试只用来评估你个人,你是否学会了所有知识,如果没有,我们会帮助你。我为什么还要去抄别人的答案呢?测试是单独的,而非公开的。”
没有什么教育是一定好的
走访了五国,周轶君意识到,教育是一种文化对人的定义。“不同的文化,长出来的人完全不一样,你说哪一种更好更有意思?真没有标准。”
周轶君对简·莫里斯《世界》里的一个表达印象颇深。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,国际新闻记者简·莫里斯在几十年间游历多国。在书里,她坦诚表达俄国人不够友好,对芬兰则观感颇佳,人都友善,社会很有秩序。
“但她说,在芬兰,如果我去餐厅吃饭,你不要指望晚餐时间坐在你旁边的是屠格涅夫。什么意思呢?她觉得俄罗斯固然混乱,但是有那么多有趣的人,从那种环境里长出来的人,有被压抑的部分,可是也有复杂性和丰富性。”周轶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芬兰人从非常好的环境长出来,但那样的人可能有点单一。咱们讲,好山好水好寂寞,他的纯洁,他的好,也有单一性。”
不同国家地域的教育状况,就像很多面镜子。周轶君说,镜子里面看到的,不应该只有差距和悲哀。“有些疯狂是应该停止的,但是也有一些文化里的发愤图强、希望更好,是不可改变的。而且那个东西一定错了吗?也未必。”
她以新加坡和新西兰举例,它们各自需要怎样的公民?新加坡可能紧迫需要精英管理人士,而新西兰更需要的是理解当地的地热资源、动物资源,懂得种植水果的人。周轶君总结,“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。国家对于公民需要也不一样,培养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。”
去新西兰采访时,一位华裔国会议员告诉周轶君:如果你把一个国家的好与坏定义为年轻人有多激进、多拼、多有钱,新西兰榜上无名。但如果把它定义为年轻人虽然胸无大志,但有自己安稳的家庭,好的人际关系,那新西兰榜上有名。
在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前,周轶君问前来参观的孩子,如何看待战争。(受访者供图)
任长箴没有孩子,也没有把各国教育方式拿回家试试的需求。在她看来,这些教育思路“只有特点,没有优点”,能效仿到什么程度,完全因人而异。
“比如德国的混龄班,在中国怎么能实现呢?咱们一个班里五十多个孩子,就这么几个老师,当然得按一个标准,最后把好生选拔出来,这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。我绝对没有一个观点说,拍了外国的教育,就觉得中国的教育都不靠谱。”任长箴说,“但是我觉得,在选拔的过程中,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培养的因素?比如加一点哲学课,培养一点感性的东西。”
观察了那么多国家的教育现状,周轶君感受到自己教育观念也在局部修正。
她出生在一个教育严苛的家庭,母亲是会计。小时候,她的数学常常考砸。在房间里听到自行车的声音,就知道妈妈回来了,免不了挨顿揍。
回忆往昔,周轶君认为,一个人很难寄希望于自己接受纯理想的教育。“你不是那么接受的部分,也是在给你将来长出一个反对它的动力积攒力量。你会很快地辨认出那是什么。”成为母亲后,周轶君尤其拒绝将孩子和他人比较,也不会无休止地要求孩子强化某一门功课,甚至因此羞辱他。“(我)对这个事情很敏感。”她说。
但埋在基因里的管治惯性难以避免。“我们小时候非常被忽视的一件事情,孩子最大的愿望是长大成人,很想像大人一样有能力,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他压制住了,我不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。”她说,“你知道家长是妄念特别多的物种。”
她回顾自己的经历,一个上海女孩,到北京念阿拉伯语系,父母虽然不了解那是什么,仍然放任她去选择。“如果我的孩子做同样的决定,学一个我完全不理解的东西,我能放心吗?”她说,她得说服自己。“现在的父母的问题在于,父母都太能了,太知道要干什么,太知道怎么规划了。”
接受采访的前几天,周轶君带儿子去爬山,爬到高处,身边人都提醒她叫孩子下来。她想到新西兰的“没规矩操场”,忍住没有叫喊。
“我觉得他可以。因为他有一点点攀岩经验,知道四个点里找三个点是稳的。我评估了一下,那个情况下,就算摔一跤,还好。就让他去试吧。”
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嘉迪
责编 李慕琰